只严肃了5分钟的加拿大存亡之战
《环球邮报》专栏作家安德鲁·科因(Andrew Coyne)3月27日撰文《加拿大的“存亡之战”大选迅速变得不严肃起来》,他质疑“两大政党的第一项重大政策宣布是什么?”,是一项耗资数十亿的减税计划——不仅会使国库资金流失,而且对提高生产力毫无帮助,甚至对最贫困群体也无济于事。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没有公平性或效率考量的跨党派贿选,是最典型的“老一套”政治操作。在国家主权面临自联邦成立以来最严峻威胁之际,我们的政治领袖却在玩选举“飞行棋”。
他指眼下这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把钱装进你的口袋”式政策,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民粹迎合。
两大党派的领导人给出的竞选纲领,竟然是取消碳税和毫无资金保障的减税大礼包。这场大选,真堪称“历史性的选择”:一个是无趣却毫无原则,另一个是恶劣却充满机会主义。
全文如下:
我注意到,所谓的“严肃时代”仅仅维持了五分钟。
你还记得吧?面对特朗普带来的“生存威胁”,加拿大政治被彻底改变了——别无选择,国家的存亡岌岌可危。我们再也不能悠哉度日,仿佛世界欠我们什么;也不能再天真地以为,我们没有天敌。
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时代需要果敢行动,需要直面现实、解决问题。尽管这场危机让人不愿面对,但它也成了促使我们奋起的动力,终结了数十年的幻想与停滞,打破了繁冗的监管和利益集团的掣肘,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政治运作模式。
我们要建造贯穿全国的输油管道,取消省际贸易壁垒,进行重大政策改革,以吸引投资并改善糟糕的生产力表现。我们要实现贸易多元化。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民主国家的防务上承担更多责任——而“民主国家”这个概念已不再必然包括美国——更紧迫的是,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国土安全。
然而,两大政党的第一项重大政策宣布是什么?是一项耗资数十亿的减税计划——不仅会使国库资金流失,而且对提高生产力毫无帮助,甚至对最贫困群体也无济于事。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没有公平性或效率考量的跨党派贿选,是最典型的“老一套”政治操作。在国家主权面临自联邦成立以来最严峻威胁之际,我们的政治领袖却在玩选举“飞行棋”。
首先“自毁信用”的是自由党领袖、曾经的技术官僚马克·卡尼。他在竞选首日宣布,将最低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5%下调至14%。这一举措显然是为了抢在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普瓦列夫之前,因为后者预计也会推出自己的减税计划。果然,次日普瓦列夫宣布,他将把最低税率降低超过两个百分点,降至12.75%。
前者每年将使政府损失高达60亿加元,后者则更为惊人,每年损失达140亿加元。而这正值加拿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时期:去年赤字已达620亿加元,今年预计仍将达到500亿加元。此外,经济衰退的阴影正在逼近,欧洲战火不断,而在北美,即便最乐观的情况也只是“贸易战”——至于特朗普的吞并幻想究竟会如何演变,谁也不清楚。
或许你会说:“至少这些政策在帮助低收入群体。”但事实上,这一减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人群:他们和所有人一样,在前57,375加元的收入上都享受相同的税率下调。而对于最贫困的人来说,这项政策根本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的收入甚至达不到纳税门槛。
这每年600亿到140亿加元的支出,全都是借来的——因为两大政党都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计划来削减开支以抵消这笔巨额财政损失,除了那些老生常谈的“削减对外援助”和“减少浪费”之类的空话(卡尼先生假装通过政府更多地使用人工智能来填补财政缺口,至少还算是个新鲜的噱头)。
这笔钱将无法用于重建我们破败不堪的军队,无法用于保卫我们的国家。它不会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会用于改善社会福利,也不会用于其他上百种更有意义的用途。
实际上,这笔钱也不会真正用来减税——至少不会用于那种能够产生积极经济效应的减税政策,比如提高工作、储蓄和投资的激励措施。降低最低税率并不会达到这些效果。尤其是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这样的减税对他们的行为毫无影响。经济学上的任何政策,边际效应才是关键。但卡尼—普瓦列夫的税改并不会影响纳税人下一笔投资、储蓄或收入,而只是对他们已经赚到的钱进行一次性回馈——这不过是一场意外之财的分配罢了。
至于低收入群体,这样的减税对他们的影响也很有限。他们本就没有多少资金可以存起来或投资。至于劳动激励,真正的问题在于高边际税率——尤其是低收入者面临的隐性高税率,比如收入测试型福利(当多赚一块钱就意味着少拿一块钱补贴时,其效果相当于100%的边际税率)。从15%降到14%,甚至降到12.75%,都不太可能对劳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如果有一种基于激励机制的税收改革,尤其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或取消特殊税收优惠来为减税提供资金,那确实值得庆祝。即使是未经财政覆盖的减税政策,如果它能够真正促进生产力的提升,也许还能被当作一种“投资”来辩护,比那些打着促进经济增长旗号的公共开支计划更有可能带来回报。但眼下这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把钱装进你的口袋”式政策,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民粹迎合。
从卡尼先生口中说出这样的政策,尤其令人失望。关于他的“人设”本应是:一位有原则的学者型人物,拥有中央银行的从业背景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危机降临之际恰逢其时地登上政治舞台,仿佛这个时刻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理论上,他的朴实正直与缺乏政治手腕应该成为优势,而不是劣势。
然而,随着每天新的投机政策出台,卡尼展现出的却是十足的政客风范——他对权力的渴望与那些从政二十年的老油条别无二致。
说到从政二十年的老油条,普瓦列夫当然也有不少需要解释的地方。他或许算得上精于算计、令人讨厌,但人们过去普遍认为,他至少是真正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不管你喜欢与否,他的经济政策会严格遵循弗里德曼学派的原则,以价格、竞争和激励机制为核心,而不是依赖监管、补贴和“免费午餐”。
结果呢?两大党派的领导人给出的竞选纲领,竟然是取消碳税和毫无资金保障的减税大礼包。这场大选,真堪称“历史性的选择”:一个是无趣却毫无原则,另一个是恶劣却充满机会主义。
卡尼先生的策略倒是不难理解。他目前领先,就像一名在迎风航线上航行的帆船手,牢牢盯住对手的每一步走向。他知道特朗普的回归彻底颠覆了这场选举,使得选民当下唯一关心的问题变成了国家防务。
他也清楚,这一议题恰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自由党的执政记录上移开,尤其是财政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败——正是这些问题曾让自由党支持率跌至谷底。但他同样明白,特朗普的影响力之所以对自由党有利,仅仅是因为这场选举的焦点仍然围绕着“谁”来对抗特朗普,而不是“如何”应对特朗普。一旦选举变成了一场关于领导力而非政策的较量,他就能最大化自己与普瓦列夫的个性差异,塑造自己为“房间里唯一的成年人”。
相比之下,普瓦列夫的策略就难以捉摸了。当然,愤世嫉俗、投机取巧这些标签本就与他相符,可问题在于——正因为如此,这样的表现才毫无新意。如果说什么时候该试图摆脱固有形象,那应该是当你把25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拱手让人成5个百分点的劣势时。
但普瓦列夫似乎无法调整战略。他之所以能一度领先,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准确把握住房和生活成本危机对加拿大人重要性的人。但他之所以失去领先地位,则是因为他过于迟钝,没有意识到过去几个月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局——特朗普回归、特鲁多辞职、自由党在卡尼的领导下重塑形象——已经彻底颠覆了加拿大政治格局。
这30个百分点的巨大变动,部分原因确实是选民对特鲁多辞职的松了一口气,部分原因是对卡尼的支持或至少是出于好奇。但很大一部分,我敢说,纯粹是因为选民对普瓦列夫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很大程度上源于两种印象:第一,他过于像一只政治斗犬,攻击性太强;第二,他在很多人看来,带有太多特朗普的影子。自由党的攻击性广告正是围绕这两点展开的,而好的攻击广告往往是基于某种事实的。
既然如此,难道不该主动远离这些“刻板印象”吗?难道不该展现出自己不是一个勉勉强强、姗姗来迟、态度含糊的特朗普反对者,而是整个加拿大政坛最坚定、最不妥协的爱国斗士吗?难道不该彻底抛弃特朗普式的语言和更糟糕的特朗普式态度吗?
他确实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在国旗日(Flag Day)的演讲,以及那支他坐在办公桌旁、全程用法语讲话、显得相对正常的竞选广告。但与此同时,他又跑去接受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采访,在言论中夹带“全球主义者”(globalist)这种词汇。这种矛盾的信号,只会让人觉得他左右摇摆、缺乏立场。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错失机会,莫过于阿尔伯塔省长丹妮尔·史密斯(Danielle Smith)的种种出格行为——她先是威胁如果联邦政府不满足她的“九大要求”就推动阿尔伯塔独立(其中第六条居然是“恢复塑料吸管”),随后又在特朗普旗下的媒体上炫耀自己如何鼓动特朗普干涉加拿大大选,声称她建议美方官员“先按兵不动”,直到选举结束,因为这场关税争端“似乎对自由党更有利”。
如果普瓦列夫想要一次“西丝特·索尔贾时刻”(Sister Souljah moment)——即像当年比尔·克林顿果断切割极端派人物那样借机展现自己的领导力——这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需要站出来坚决捍卫加拿大的统一和独立,他就能轻松拿下一场“空篮灌篮”。是的,也许这会让他在阿尔伯塔损失一些选票,但顶多是从80%降到60%。相反,他可以在全国其他地方赢得更广泛的支持。
但他却什么都没做。他只是干巴巴地说,史密斯的要求是“合理的”。至于她疑似与美国共和党串通干涉加拿大选举?他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
也许他担心这会打击自己的基本盘,也许他害怕给人民党(PPC)留下可乘之机,甚至可能只是因为他真的挺喜欢史密斯。但无论如何,他在全国选民面前表现出的,依旧是这几个月来最常见的样子:软弱、犹豫、迟钝。
说真的,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说出这句话——普瓦列夫的问题,难道是他还不够冷酷无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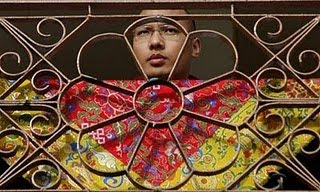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